《海州文旅之声》| 第九十八期
走遍海州 是身体的旅行
访遍老友 是心灵的探寻
枕山襟海 品位文化
与文化相伴 美好触手可及
——《海州文旅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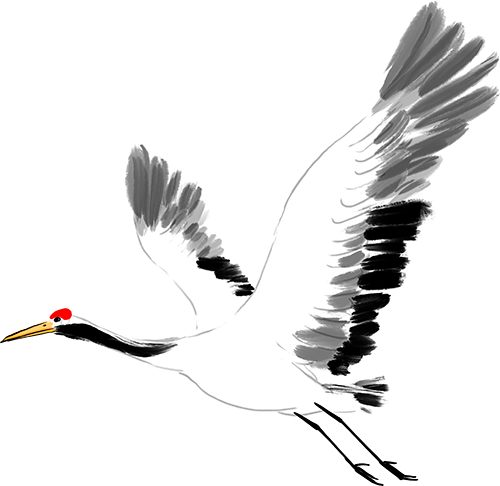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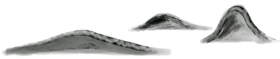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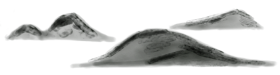

不知不觉已经临近端午节,一种平时几乎无人问津的食材在这段时期变得“身价百倍”——芦叶,是海州地区包粽子的主要材料,早年许多人家会选择自行采摘,叫“打粽叶”,而现在还坚持自己包粽子的城市居民全都要从市场上去采购了。至于出产这种粽叶的芦柴地,也只能向城外去寻觅了。
老苍
昨夜我又梦见了老家那一片芦柴地,在风的摇曳下那绿色的柴叶在频频地向我招手,把我引进了星罗棋布的柴地纵深之处。那像迷宫一般的小路穿梭在芦苇的间隙中,贴着圩塘两边的沟水左转右转,七拐八绕,让你不知道从哪一条小路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可以看到水里的鱼虾在冒着泡,你的耳边能听到呱呱鸡的唱歌和癞蛤蟆跟青蛙发出的和声。你能瞅到芦柴上一个个水鸟搭的窝,到了近前看里面会有三五个的鸟蛋,你还能见到柴地上长着一种叫“大馍馍”的野生植物,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很好吃!风吹芦苇,惊飞只只水鸟,一首熟悉的童谣响于耳旁:呱呱鸡,你家住在哪里?我家住在芦柴地,吃什么?吃烂泥。

芦荡里尽管路有数条,但你只要记住每条路的特点,你就能轻易地沿着柴地里的水路走出迷宫,在柴地环绕的中间一个高坡之间发现一个不大的村落,小的只有三五家茅草屋。庄里的狗闻到了生人味就会叫唤着冲到你面前上蹿下跳,接着你还会招惹那些鸡鸣、鸭唱,还有那“曲项向天歌”的大白鹅的过分关注。听到外面吵闹从土房里走出的年迈老人,大声喝止狗仗人势的畜生,昏花的老眼上下打量着你,半天才能认出原来是新浦的侄儿走亲戚来了。于是高兴地接过你手中提的茶食,把你领进顶上瞅不见一片瓦,只用圩塘里生长的大柴和毛樱花盖起来的屋中。
我梦见的不是现在新宅基上那砖石到顶的钢筋水泥堆积的三层楼房,说也怪,我这几十年每次只会梦见回到十多岁时四周都是圩塘的旧宅。那才是我的根,也是我父辈梦魂萦绕、远离故土千万里也会时时惦记于心的故居。

我的父亲兄弟两人,父亲在新浦解放那年参加解放军离开家乡。乡下的二爷伴随着祖母一直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父亲每次从大西北回老家都会带上我,那种近乡情更怯的感情,那份对家乡泥土的挚爱,也浸润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喜爱那被芦苇荡围起来的乡村房屋,我更喜欢和老家的哥哥、弟妹们钻到芦柴地里去逮鱼摸虾、藏猫猫。我喜欢二娘在蒸馒头时弄上几片柴叶放在馒头的下面铺垫着,等揭开锅盖你就会闻到柴叶的清香味,那蒸出的馒头也是带着柴叶的余香。我更喜爱年迈的祖母把玉米棒插入火叉放入锅灶的柴火上烧,把黑乎乎的玉米棒从火塘里取出,用嘴使劲吹着,还用她那双粗糙的手弹掉上面的锅灰,做完这些才放心地把玉米棒送到我的手里。此情此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也是我在多少个夜晚常温的香甜梦境。
随着端午节临近,少年时在老家过端午节的情景也会常常闯入梦乡。五月端这天,小女孩手脖上会系上红丝线,脖子上会挂上香荷包。祖母和二娘会把五月红的萝卜削成片放在盘里拌上白糖,会在黄瓜里塞矾吊在屋檐下晒,说是这天黄瓜矾晒好后,以后嗓子眼起个疮、上个火,用它按些在疮口上就会好了。
五月端包粽子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包粽子的芦叶房前屋后就有。我们老家的芦叶又宽又大,三片粽叶就能包一个大粽子。打粽叶的活就由我们这些孩子揽过来,小姊妹们也不怕蚊子咬、蚂蟥叮,一个个嘴里哼着七高八低的小调,一边从芦苇上挑选着没有虫印、三四指宽的芦叶。有的小姊妹闲不住就会拽下一片叶子,从中间分成两半叠成风吹,叠好后劈上一根芦叶用芦芯穿进风吹中间眼子里,再把柴芯的头子系上扣子迎风一摇,风吹就吱吱地转动起来。口渴了就从水里拔上一根很嫩的大芦苇洗去淤泥,嚼它的根子,就跟那街上卖的甘蔗一样的甜。
柴地沟里到处都是宝贝,吞呱呱鸡蛋、抓小鸟、摸鱼虾,下水捞那些野鸭子和家鸭子下在水里的蛋。我最喜欢长在大芦苇上拖得长长的“大馍馍”,那味道有独特的甜润、清香,吃在嘴里回味无穷,已经五十多年再没有尝过了。

芦叶打好后,大人们把它剪得差不多一样齐整,烧一大锅水,把芦叶一把把地在开水里烫一遍,这样叶子包起来有韧劲。一般包粽子都是用糯米包,放上蜜枣、花生、红小豆,肉粽子没有人家舍得包。我们老家当时不长水稻,想吃米就用黄豆和小麦去公社的粮管所换。有的人家不想这样麻烦,就用芦粟(也就是高粱)代替。现在乡下都不种这玩意了,当年老家地头这种黏芦粟被风一吹红浪翻滚十分好看。冬天把芦粟加成粉,用它替代糯米面,包出的汤圆在草锅里烧开了浮起来,满锅都是红彤彤的圆球,看一眼就让人很有食欲。去年一位亲戚曾送给我五六斤芦粟粉,我用它包了元宵,感觉比糯米粉包出的还要香甜,于是我又转送了一些给我的父母姊妹尝了鲜,她们也是几十年没有吃到这种稀罕货了。老家的人到了五月端包粽子时也会用芦粟包粽子,比糯米还要黏。

五月端的早上,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鸡蛋和粽子一块吃,大人叮嘱我们要在太阳没出来前吃粽子和鸡蛋,以后腰就不会疼了。吃完了粽子和鸡蛋后,大人还要把艾草熬水给我们洗澡。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一天正午时,我们脱光衣裳,从烂泥塘里挖出泥来,你向我身上抹,我往你身上擦,一个个抹得就剩两只眼珠滴溜溜地转,还有张嘴看到的两排白牙。然后躺在河边晒太阳,五月端这天正午时的太阳很毒辣,晒得这些傻小子身上的泥一块块地从身上掉下来。等正午时过去,身上带着残留的泥巴,一个个像下汤圆似的跳入河里……
转眼间我们都做了爷爷、奶奶,几十年的光阴让我们这一代人青春耗光,也让老家的水土斗转星移了。现在回家再也看不到一望无垠的芦苇荡,也找不到土坯屋了。城市化的推进让乡村空间缩小了。我的那些兄弟姊妹都从老宅基上被规划到新农庄竖起的一栋栋楼房中,家里的装饰一点也不比我们住在城里的差什么。我的好几个叔伯弟兄都在城里买了楼,乡村剩下的多数都是年老体衰和那些对故土难舍的念旧之人。
随着老一辈的人一个个离开,今天的年轻人对这些传统的节日已经越来越淡漠了,也就我们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过来之人,还记得一年之中有几个传统的节日,还会时不时地在肚子里把旧时的一些事情经常颠来倒去一下。于是,你只能带着你的满肚子往事,数着满天的星星慢慢睡着了,去和那一片片芦苇地重温旧梦。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现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来源 | 连云港广电广播传媒中心
连云港广电教育传媒中心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