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文旅之声》| 第二十四期
2023-02-23 18:00:14
走遍海州 是身体的旅行
访遍老友 是心灵的探寻
枕山襟海 品味文化
与文化相伴 美好触手可及
——《海州文旅之声》



古人取名很是讲究,不仅有名,还有字,有的还有号。现代除了一些文人雅士之外,很少有人再起字、号了。但许多人一般也会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大名,一个是小名(也称乳名)。小名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的不同,有很浓郁的地方特色。今天就来说说海州起小名的习俗。



崔月明
现在人起小名,也并没有什么讲究,一般只是表达父母的愿望,或者为了一个纪念,或者就是触景生情。如我的女儿出生在春天的一个早晨,当时外面正下着小雨,取雨露滋润万物之意,小名便叫“露露”。有的人家干脆就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相叠,如“玲玲”“雯雯”等。现在人的小名一般只在家中或很要好的朋友中使用,叫起来非常亲切。
过去,海州民间每个人都有小名的。孩子生下来三朝就要起小名,也叫起“乳名”。海州有句俗话:丑孩鬼不要。就是说丑孩子好养活,所以,小名起得越丑越好,越怪越好,如“小秃子”“大癞子”“小驴子”等,有的干脆就叫大丑、小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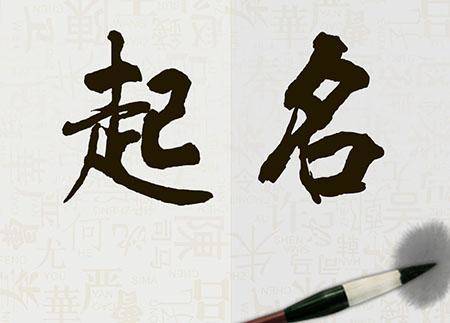
起小名一般根据孩子降生后父母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或者父母心中的愿望。如有的人家把孩子的衣胞埋在路口,就起“路生”“大踩”“小踩”;有的人家在埋衣胞的罐子里放些黑驴毛和炒熟了的芝麻,意为“衣胞带芝麻,能活九十八”,就起“大驴”“小驴”“大芝”“小芝”;有的人家用一根红线扣在孩子的脖子上,就起“大扣”“小扣”“扣住”;有的人家用银锁在孩子的脖子上象征性地套一下,就起“锁成”“锁住”;有的人有用一口铁锅在孩子的头上罩一下,也叫“卡一下”就起“卡住”“铁头”“铁蛋”,铁锅卡过孩子之后,要从屋顶上扔到家后去,摔得越碎,孩子的运气就越好,叫做“贵人撑破铁,能成大事业”。有的父母望子成龙,希望孩子将来能做官发财,就起“大富”“大贵”“大升”“大发”;有的人家想要男孩,就把上一胎女孩起叫“招弟”“迎弟”“盼弟”“来弟”;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女孩,也没招来一个小弟弟,就给新生的孩子起名“小改子”“小转子”“小换子”;过去人不懂得计划生育,有的人家孩子多,不想再要了,就给孩子起名为“小停子”“小满子”“老搁子”。
有的人家按时间起名,如“大冬”“大春”;有的依属相起名,如“大虎”“大龙”;有的以出生地起名,如“新浦”“海州”“锦屏”等。
刘姓、陈姓、石姓与“留”“成”“实”谐音,被认为是“吉姓”。有新生儿的人家,千方百计地去偷这些人家的煨罐,好用来埋衣胞。偷了煨罐之后,希望被偷的人家骂,骂得越凶,孩子就会长得越壮。因此,孩子就起名“大罐”“罐住”等。
男孩子到七、八岁上学,或者十二岁入宗谱时起了大名,小名才不用。有的也一直用下去,或者就当着大名用。女孩子除了名门闺秀能够读书的,会起个芳名,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大名。
井,指的是从地面挖出的取水的深洞,现代人对它已经没什么观感,而在旧时,却是人们生活的必备设施,于是被引申为家乡的象征,于是就有了“背井离乡”这个词,用来表达人们远离家乡寻找新生活的复杂情感。所以,井,寄托了人们对于家乡的眷恋和牵挂。
作者:潘友国
板浦汪宅有一眼老井。汪宅,它坐落在新民路西顾巷。汪宅也就是汪家大院。西顾巷,是一条长大约七十米的老巷,四通八达,南通影壁巷,西通栅栏巷,穿梭巷中,找不到出处,宛若迷宫……两侧房舍建筑,基本上是明清徽派风格,石板路,青砖黛瓦,飞檐翘壁,花格雕窗,大红灯笼高高挂,古朴沧桑。
有些地方会吃,似乎是天性。比如:古镇板浦。古镇,算得上是美食荟萃之地,因此,从古至今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穿海州,吃板浦,南城古财主”。
巷口头,有销售凉粉的。凉粉最乡土、接地气,乃古镇经典小吃,好吃到欲罢不能。凉粉很走俏,摊前,食客排成了长队……买到凉粉的喜上眉梢,没买到的则耐心等待。

西顾巷,其巷内的汪家大院,坐北朝南,陈旧的门额上题有“汪家大院”四个字,龙飞凤舞、字大如斗,非常醒目。院门后,一堵影壁墙,影壁墙的正面嵌有一个“福”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影壁墙的功能主要是辟邪,过了影壁,接着往里走,就可以看到一口井,深而直,历久弥坚,且纤尘不染。井水格外清亮,清澈见底,井面犹如明镜,照见蓝天白云,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掬捧入口。饮上一口,味如乳,甘美甚。
井下有泉眼,泉水很旺盛。井水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汲而不竭。院子中的老屋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显得破旧不堪。
院子虽大,却静得出奇,没有鸡鸣狗吠,没有喧嚣声,充满了阳光。
院子里还有惹眼的看点:一株斑疤虬曲的石榴树,罩于屋顶,清寂中显出蓬勃生机。石榴树也有些年头了。夏天,烈焰似火,开一树的繁花累果,照人眼明。在民间,石榴树是吉祥物。
现今,汪家大院成了最有价值的存在,它是古镇历史的见证。汪氏一门走出了“两弹一星”元勋、细胞生物学领军人物、中科院资深院士……在古镇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乡之水,必有其源。
汪氏三兄弟,沿着西顾巷的青石板,背起行囊,背井离乡,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古镇,去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水之井就成了历史之凹,时光流转至今,那眼老井,依然鲜活着、光亮着,汪着乡情也汪着水情。可对于汪氏三兄弟来说,离乡久了,难免生出一丝惆怅,不由得起了乡愁。故宅那一汪碧水,已经深深地浸润在他们的血脉中、骨子里。
是的,终究,月是故乡亲,井是故乡甜。于是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三兄弟结伴而归,不远千里,回古镇寻根来了。他们一踏上故土,就先在巷口头,吃上一碗凉粉,味道跟以前一样,劲道、爽嫩、富有弹性、滑而不腻。
再饮一口老宅的井水,就足以慰藉乡思了。饮时,颇不知那眼眶里,大颗大颗滚烫的泪珠,早已顺着脸颊滚滚而下。井水和泪水,相融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井水,还是泪水,喝上一口,感觉有点苦涩的、咸咸的,却又盈盈的,透出一丝甘甜……
古镇,因汪氏三魁,享誉中外,声名远播,汪氏三兄弟为古镇写下了璀璨一页。时至今日,汪氏三兄弟的名字依然在古镇的星空,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古镇井文化,深邃隽永。井脉就是文脉。
张文宝先生在《汪氏三兄弟》一书“代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板浦历史的深井很深很深……汪氏三兄弟离开板浦老家已很久很久了,可汪家院中的那口小井还完好如初地在那儿,一井碧水,晃晃悠悠……
井之功大矣。
在我的心目中,汪宅的老井是古镇最有特色的风物。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现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来源 | 连云港广电广播传媒中心
连云港广电教育传媒中心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