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阅美 |(60)《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第十六章 站在高山大海之间(第一篇)


点击收听
《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
简 介
在贫瘠乡村燃起教育启蒙的烛火,散尽家财组织抗日武装,枪林弹雨中奔走的“游击校长”……在苏北鲁南现当代教育史上,他的名字不可磨灭。从20世纪20年代创办第一所乡村学校开始,他便将革命教育视为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从乡村教育到国难教育,从战时教育再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他创办或领导的十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他就是郇华民,一个毕生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实干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的道德品行,将革命教育的火种燃遍苏北鲁南;他把党的事业、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泰山,以异于常人的坚守和操劳,沉淀出丰厚的精神沃土,成为苏北鲁南地区现当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文艺精品项目——长篇报告文学《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学会常务理事、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主席王成章,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连云港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韦庆英历时三年深入采访,倾情奉献;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连云港市档案馆荣誉出品,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
第十六章 站在高山大海之间 第一篇
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顿挫吧。
1966~1976“文革”十年,整个教育领域受到重大影响,学校课程与教学经历了一场灾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各地学校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声讨其滔天罪行。
1977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把春风吹进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田。5月24日,对外贸易部发出《关于加速利用连云港问题的通知》更让港城知识分子嗅到了科学发展的气息。许多老同志见面相互间有了笑脸,这笑脸不是只为了彼此的际遇变化,更多是为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此背景下,各地各单位纷纷成立“顾问组”或者“顾问委员会”,将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聘为“顾问”。
1979年10月,连云港市教育局也成立了“顾问组”,“顾问组”由郇华民任组长,成员有:李黎民、桑淑尊、刘汉章、杨竹铭等人,都是解放后全市各重要学校长期担任领导的老校长或教育部门老领导。教育局为“顾问组”召开了隆重的大会,教育局的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各区文教局的领导和市属学校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局长为每位成员颁发了《顾问聘请书》,教育局为“顾问组”安排了办公室,还配了一部小车,说车子是“随叫随到”。老同志们“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可顾问们断不肯给越来越繁忙的教育工作添麻烦。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安分自守”、“安贫乐道”、“安度晚年”三个词语成了一帮老同志走出“牛棚”成为“顾问”之后的互勉。

1980年代连云港市教育局五位离休干部(右起:陈洪玉、李黎民、刘汉章、郇华民、李效峰)
1982年,郇华民搬家到教育局在新浦龙尾河畔为职工盖的小院中。自此,75岁高龄的郇华民告别了校园生活。老“顾问”们本来就喜欢到郇华民家里“顾问”,有了一个独立的“小家院”,他们就来得更勤快了,从一个月一聚改为半个月一聚,队伍也不断扩大:有几个年轻一些的不是顾问组成员的退休教师或校长也来了,电大的陈振伦、教院的沈伟民、墟沟中学的徐邱、朝阳中学的方文光以及海师的张云明、徐晓非、宋健民等。他们每次来,朱崇芹虽然要上班,但都提前给烧好开水,备好时鲜水果蔬菜,让他们开心小聚。
任职“顾问组组长”期间,郇华民公私分明,从未因任何原因给公家添过麻烦。这个党性极强的老共产党员常常和老朋友们说:“老了老了,就要认老!不添麻烦就是做贡献啊!”
有一次郇华民重感冒,发热、头疼、四肢无力,必须上医院就诊。那时新浦街上没有出租车,郇老所住的龙尾河畔那一段,也不通公交汽车,怎么上医院?和老人住在一起的郇春生说:“我借平车送爸爸去吧。”郇华民说:“你快上班,我只是感冒,没大事,你们上你们的班,由你们妈妈陪我去就行了。”朱崇芹说:“要不,咱给局里打个电话,请局里派辆车来吧?”郇华民坚决不同意:“生病是私事,哪能麻烦局里?”自己拄起拐杖,叫朱崇芹扶着他慢慢向医院走去。
在通灌路上,遇见陈振伦骑车经过。他看见郇华民一脸病色,艰难地向医院缓缓移动,便问道:“郇老,咋不要个车?”郇华民淡然一笑说:“安步当车,活动筋骨,益寿延年,不亦乐乎?”
有一次郇圩小学想请他回故乡去给孩子们讲革命历史。朱崇芹说:“这算是一件公事,不通车,路又远,让教育局派个车不算过分。”可是郇华民仍然没同意:“这是我家乡的小学怎能没有点私人的因素?再说我回去后还要看看乡亲们,我也真想他们啊!我们坐火车到牛山(东海县城),让耀中用自行车送我们去郇圩吧。”
朱崇芹只好与郇华民坐火车到牛山。郇耀中借了两辆自行车,一辆给母亲,一辆自己带着父亲,一行三人回到了郇华民梦萦魂牵的故乡。来到郇圩小学,郇华民里里外外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同学们热情欢迎郇爷爷回来,还演出文艺节目给他看;郇华民与教师们交谈,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待遇等情况都问了个遍。看到学校还有六间危房,心中也非常着急;看到学校图书室中空空如也,没有几本儿童喜欢的书籍,更加难受。他和乡亲们嘘寒问暖,促膝谈心,乡亲们也祝愿他健康长寿。
回新浦后,他叫朱崇芹到新华书店买了二百多本适宜儿童阅读的书籍,寄给郇圩小学。花钱虽不多,但这是他对家乡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有人要把他购书助学这件事报道一下。他阻拦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张扬什么啊!”
从长孙女的文章《祖父百年》中,可以看到她眼中祖父1980年前后的几个生活片段——
我记忆中的祖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从海师这个场景中出现的。此前对祖父经历的曲折磨难,童年的我并没有多少了解。我的父母在东海工作,每逢假期或有空时,就要坐火车到海州来。海师的大门是向北开的,拾阶而上,就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花园,一个植物的天堂。祖父经常牵着我,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告诉我那些盛开或凋零的花事。
祖父家就住在校园内大门东侧的一排平房里,相邻住着几家教职工。家门前是几棵伞状的高大的核桃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伸手就可以摘到累累的核桃,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摘过一颗。公共厕所在校园的西部,要去需经过一片果林,栽满了苹果树和梨树,从果林中间的小路穿过,成熟的果子在头顶跳跃,我竟也没有吵着要过其中的一个!校园东部操场边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为了遮挡东部围墙外的民舍和荒丘所植。
校舍前后到处都是花园,是学校在花园中,不是现在的花园在学校(或单位)中。春日里桃花、李花、杏花、牡丹、芍药争奇斗艳;夏日里睡莲、紫藤花静静地盛开着;秋日高耸的银杏树层林尽染,黄金满地;冬雪覆盖时苍松绿衣青翠,顶着满头的“白发”。花的色彩固然绚烂,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花香。春天几丛木香盛开,白色的繁花缀满枝头,招蜂惹蝶,清香浸满了整个校园;中秋时分桂花馥郁的幽香沁人心脾;最难忘的是寒冬里的腊梅,暗香浮动,冬日里绝美的芳菲。
校园里还栽植着一种树叫紫薇,树干莹滑光洁,开着粉紫色琐碎的小花,开花时正当夏秋,且花期极长,由6月可开至9月,故有“百日红”之称,又有“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的赞语。祖父说那叫“痒痒树”,为了示范,他用手轻抚树干,果然枝摇叶动,枝头的花也“悉悉索索”地晃动着。
祖父前半生在为革命奔波,后半生教书育人,从没有学过规划或园林,却深谙造园的精髓和环境育人的真谛。上大学时,我常携一本书在苏州的某个园林待上半天,那时人流没有现在的喧嚣,那时我就在想念海师的校园,较之一些苏州园林的狭小和局促,海师显得更加大气、灵动而有生机。
孩童的记忆除了玩就是吃,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到祖父家能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是喜欢来的原因之一。虽然那时的美食在现在的小孩子看来可能都不值一提。
祖父喜欢吃甜食,这个习惯遗传给了多个子孙。家中自制的糖饼特别令人向往,这糖饼有一个铁制的两片相对带花纹的圆形模具,还有两根长长的手柄,把发好的面团包上芝麻和糖,放进铁模夹好,放在碳炉上两面慢慢地翻烤,就会烤出焦黄喷香的糖饼来。最招人欢喜的是那饼上精致的花纹,捧在手中不忍破坏它,绝不同于现在街头烙的发面大饼,即使放了糖也还是那么粗俗不堪,难以下咽。有时候嘴馋得很,祖父就把做饼的糖提前给了我吃,等到做饼时发现糖罐已经空了。
经常有祖父的朋友或学生从外地来拜会他,带来些稀罕的点心,祖父就分给我们吃。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北京的茯苓夹饼,以茯苓霜和精白面粉做成薄饼,中间夹着用蜂蜜、砂糖熬溶拌匀的桂花蜜饯松果碎仁,有着获苓和桂花的清香,舍不得一口吃掉,总是细细地品尝。长大后时常怀念它,家人出差去北京,必定叫带几盒回来,但怎么吃都有一股陈年的樟木箱子味。
“八宝饭” 和“虎皮肉”也是祖父爱吃的食物。“八宝饭”是用糯米、赤豆、栗子、银杏、花生、百合、莲子、蜜枣等食材放在一起蒸熟,再拌上蜜饯和山楂条,香甜可口。最见烹调功力的是奶奶做的“虎皮肉”,把带皮的五花肉切大块放到开水里氽到八九分熟,捞出来用酱油和蜂蜜抹匀,腌制半天到一天,收干水分后放到油锅里炸,炸到表面黄而不焦,取出后切薄片放葱姜糖等调料,再放进蒸锅中用大火蒸透,油亮光滑,纹似虎皮,软烂醇香。
祖父爱吃的还有老家东海的柿子,这是漤过的柿子,橙黄的、软软的,有着吹弹欲破的皮,揭开一个小口就可吮吸里面甘甜的汁液。还有一种是大果子,类似现在街头卖的京糖果子,但个头要大得多。而祖父的家常饮食早上不过是一瓶牛奶,一两个鸡蛋而已。
祖父的家居生活是简单而朴实的,无论是在海师还是后来搬到新浦,从没有豪华的装修和装饰,极简单的木制桌椅和茶几,椅子是藤编的,布艺的沙发用了多年,里面的弹簧坐上去硌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也只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这几样基本的电器。衣着都以棉布为主,常穿的是蓝色或灰色的卡其布做的中山装,平实中透着温暖。在海师住的房子是平房,厨房在对面,中间没有过道连接,下雨天要经过雨地才能到达厨房。为了避免屋檐下的雨滴,用一根毛竹劈开两半,取半边挂在屋檐下接水,让水从一头流出。厨房是两家合用的,互相可以看到对方每顿在吃什么。后来搬到了新浦,三间平房一个小家院,一家老小近10口人住在一起,拥挤且不说,夏天下大雨的时候,房子进水,需人工防洪排涝。大水过后,家里总是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祖父除了读书看报之外,就是侍弄花草,拔草除虫,浇水施肥。门旁是两株腊梅,窗前玉兰参天,院墙上爬满了凌宵花,迎春、樱花、百合、海棠恣意地生长盛开着,这个垂暮的老人渐渐地力不从心。
祖父有子女五人,孙辈九人,重孙辈七人,祖父在世时,最大的两个重孙刚刚3岁。在儿孙当中,不少人怕见祖父,因为他诲人不倦,只要见面就要从《四书》《五经》讲起,直至当前国家大事。他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些国学知识强调学习的方法、内心的修养和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尚可理解。但祖父还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不仅向子孙讲,但凡有学生或朋友拜访,他都要把他最近学习的心得与人交流一下。当时的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祖父要向他身边这些平凡的人去教授治国之道,多年以后才明白祖父“位卑未敢忘优国”的真意,也才了解许多学生和亲友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有不少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学子因他的指点确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祖父注重内心的完善和自身的修养,他“不怨天,不尤人”,从来不去苛责命运和环境,以宽厚仁慈的心来对待家人、学生、同事、朋友、甚至责难过他的人。祖父的一生向我们传授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朴素温暖,从容谈定的生活态度。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FM90.2广播
每天15:30~16:00,20:00~20:30
《悦读阅美》栏目中将播出
长篇报告文学
《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
欢迎收听
本期朗读者:葛小琴
美 编:王 哲
扫二维码查看光明日报报道版面

编辑丨王婷婷
审核丨段潇
来源丨FM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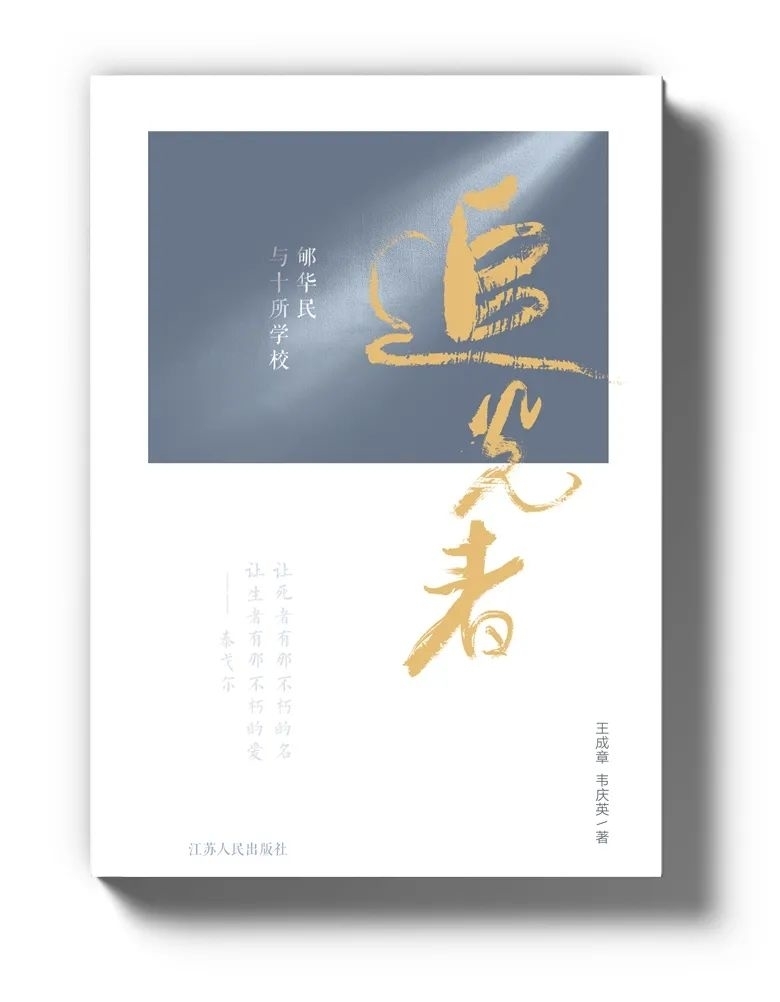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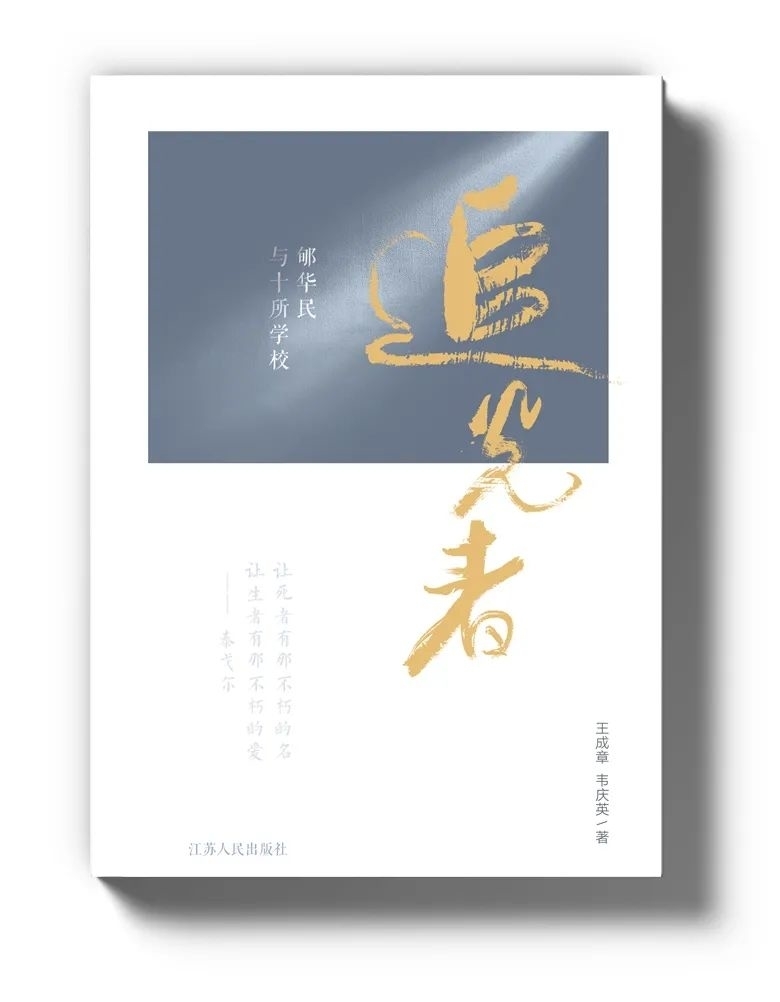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