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山散文集《家在龙尾河畔》第七章第七节|奇人冯景昶

「家在龙尾河畔」|第七章 第七节📖

▾ 点击收听 ▾
《家在龙尾河畔》简介
2020年,一部名叫《家在龙尾河畔》的自传体散文集诞生了,书的作者叫张耀山。作品诞生之初是非常之年,诞生之际是非常之时,诞生之作是非常之举。因为这样一本书的问世与这个年景的许多元素有着高度的契合,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家在龙尾河畔》始终以平民生活为底色,热烈地拥抱生活,处处可见血浓于水的家乡情节,绝不像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找不到自己的原乡。正是那些琐碎的、点滴的生活细节,构建了作者极尽渲染的龙尾河畔泛黄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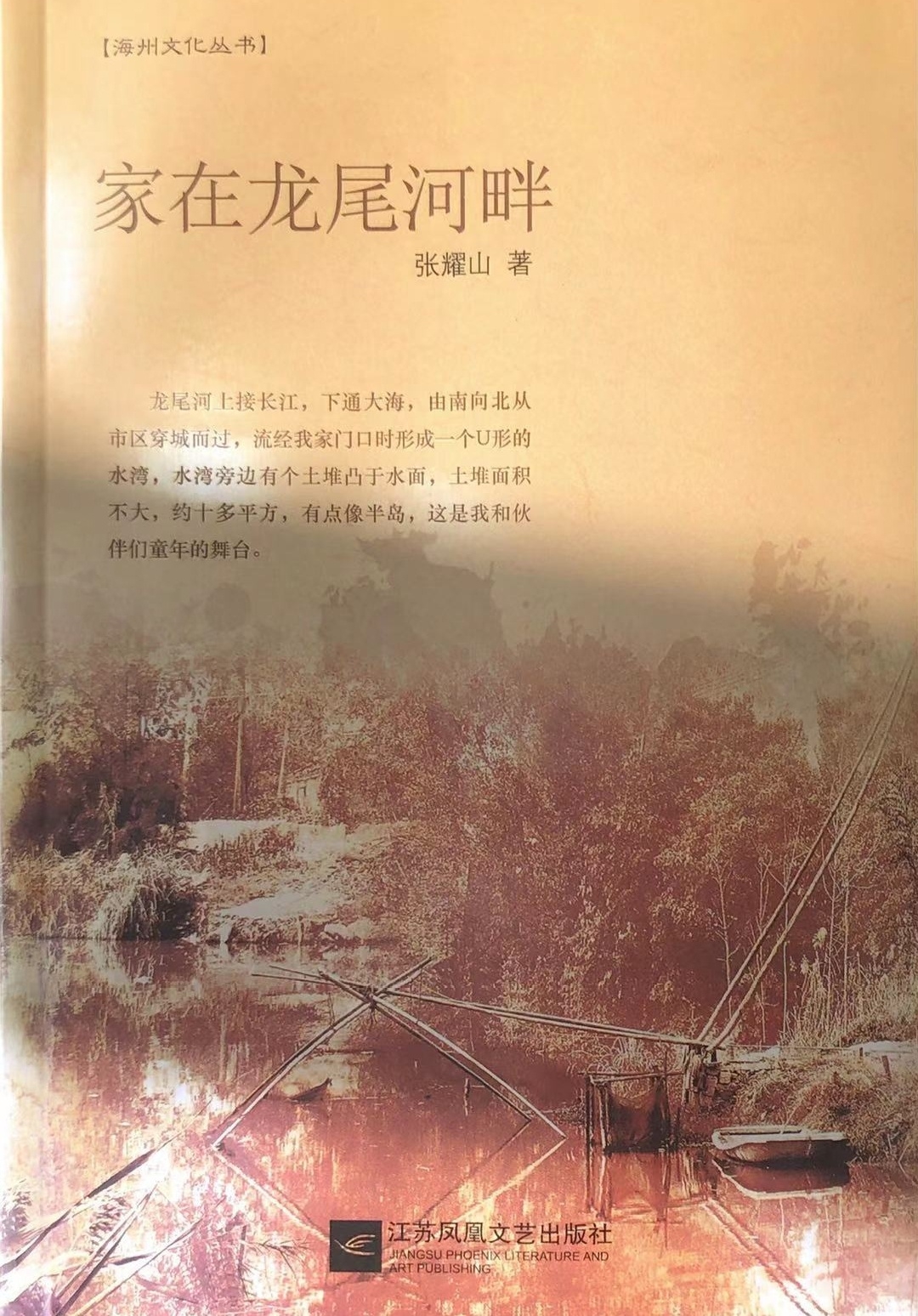
- 关于作者 -
张耀山,1955 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生于连云港,曾就职于连云港市文联。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十三届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连云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连云港市安东书院院长、连云港市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他认为家不是由物质堆砌起的空间,家是情感的载体,是灵魂的栖息地,是精神的乐园。

奇人冯景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经济转型期,各行各业都在挖掘自己的优势,想方设法赚钱。作为"清水衙门"的学校,它的优势在哪,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小学领导在苦苦思索着,他们要盘活学校现有的资源,为广大教师谋福利。学校放假教室闲置着,这触动了他们的灵感,发现了商机。将三四线城市的同行们吸引过来,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此同时三四线的老师也有利用漫长的假期走出家门散散心的需求。供求关系,一拍即合,实现双赢。
1982年暑期,当时我在建国路小学当老师,我的同事的亲戚在北京北海公园后门附近的学校做领导,通过他的牵头,我们学校男男女女四十多号人来到了北京,对于多数人而言第一次来北京既激动又开心。窗户挂上窗帘,课桌上铺上凉席,早晚提供几壶开水,这是对方为我们一行提供服务的全部内容。旅游的形式是宽松随意,自由组合,各自行动,不作统一安排。在此之前我曾有独自去杭州上海等地旅游的经历,对于景点的选择、车次的转换诸方面比较熟悉,所以好多老师认为我有经验,喜欢与我同行。
来到北京,故宫、长城、天坛等知名景点当为首选;王府井、东单、西单为女教师的最爱;北京动物园是带孩子来玩的老师不可略过的景点。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不亦乐乎。
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北京,但所游的景点都挺熟悉,身临其境,只不过是为了印证一下它的真实存在、走完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而已,无惊也无喜。
拜访冯景昶先生是我这次北京之行的意外收获。陈凤桐老师听说我要去北京,建议我去拜访一下冯景昶先生,此时陈老师正在编辑《当代楹联墨迹选》,约请他为该书撰文写序。 据说他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当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他收藏了很多古代的名人字画。
他家住北京旧帘子胡同,打开地图查一下,距离荣宝斋不远,因而确定了我在北京最后一天的行程。 在去北京之前,我一直以为北京的夏天是很凉爽宜人的,毕竟是北方城市嘛。到了才知道,北京热得让人无可奈何,没有一丝风,老式胡同里没有一点绿。黑砖黑瓦的四合院,吸收大量的热能向你迎面撞来,沥青路面释放的热量顺着两条裤管向上蹿,整个北京像是一个巨大的烤炉,吸干你身上所有水分。
按照陈老师提供的门牌号码,我来到了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内,院子面积不大,拥挤着三五户人家。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见有生人到来,前来盘问,我说明来意,她京韵十足地喊冯先生的名字。我站在冯老先生家的门口,听到屋内有动静,门帘却迟迟没有撩开。过了好长时间,一个花白头发、戴着高度近视镜,一看就是满腹经纶的老者探出头来,伸出右手,十分热情地把我让进室内。与室外刺眼的光线不同,室内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好长时间才适应,看清了室内的摆设。让我扫兴的是与事先勾勒的场面大相径庭。
我原以为这么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问家,祖上世代为官,整个旧帘子胡里应为冯家独自拥有∶推开院子大门是一道照壁,上面有精美青砖镂雕,萧墙的背面矗立合乎"漏透皱瘦"四美的太湖石。小院子不大,一条窄窄的甬道通向后花园。堂屋的迎面墙上悬挂着出自"四王"某人之手的山水中堂, 两边配上翁同稣或刘石庵的楷书对联,红木条几上摆上一对景德镇瓷瓶,博古架上放满线装本, 画桶里插着几卷画轴。没想到眼前的一切如此简陋∶ 整个房间面积最多六七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加上一把椅子,占据了房子的大半,其他地方有脸盆架和一只带烟囱的小煤炉。煤炉上一只铁勺子里煎着鸡蛋,不知是充当早餐还是午餐。他觉得在接待客人的时候煎鸡蛋有失礼节,不停向我表示歉意,再三给我让座。床上堆满了书,大热天床上还铺着裘皮,我的屁股只能搭在床沿边上,膝盖抵着前面椅框,十分局促别扭。他穿着大裤衩,上身穿着白色的短袖衫,让人称奇的是短袖衫从底摆到领口是一条长长的口子,用颜色反差很大的线连缀起来。其实在北京见怪不怪,大老爷穿着大裤衩,赤裸着上身满街晃悠是常态,没有人认为这是不文明现象。像冯先生在家接待一位男性客人,光着上身也不为不恭。煎鸡蛋的油呛味和煤炉里散发出的油烟气弥漫着整个小屋。
他知道我酷爱书画,很遗憾地告诉他家祖辈珍藏好多古人字画,前几年连同祖上的房产全被抄走了,现在落实政策,正在办理交接手续。他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下次再来,一定让你饱饱眼福。
我觉得我的到来有些唐突,在他说话空隙,我把陈老师交代给我的事与他交接完毕,想尽可能早地结束这次造访。大老远地跑来又匆忙要走,这让他深感愧疚并再三挽留,不停地向我道歉。他问我下一站的去向并撕下当天日历在其反面画路线图,因为所画线路的比例不够准确,他又撕第二张日历,拿在手里时反复念叨这是明天的日历,稍做犹豫,他又画了第二张。他指着画好的线路图告诉我,从这向东多少米是人民大会堂,向南多少米是前门车站,坐几站地到沙滩即中国美术馆,再向西多少米到你的住处。像是家长在交代上学第一天的孩子。急性子的我遇到慢性子的他,无计可施。他牵着我的手走出堂屋、院门、巷子,拐弯抹角不知走了多 远看到了人民大会堂,我想这该放心了吧。在我再三请求下,他终于撒手了,我也算松了一口气。我走了几步回头向他打招呼,他向我作揖致谢;我走了几十乃至几百步回头看时他仍在原地作揖致谢。中午的阳光无遮无拦倾泻在空荡荡的小路上,只有我们两人在隔空招呼着。我不忍心再回头了,看路旁的巷子里有块阴凉地,想过去避避暑,也好让他回家。没有两分钟,他再次出现我的面前,再次抓住我的手,手牵手一直来到前门车站。
前门车站靠近天安门广场,有多次班车在此停靠。挤上班车后他仍在不停地打招呼,说些什么听不清楚,隐约感觉到,我第一次来北京让他放心不下,生怕我走丢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叙述这段经历时仍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他给我的印象是学问渊博而有点迂腐,待人热情而几近溺爱,历经坎坷而心底洁净,固守传统,是个讲究礼数的人。他语速很快,举止却慢条斯理,是个可敬可爱又可笑的老夫子。于是我关注了他,并拜读他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如《当代楹联书法简章作品选 迹·序》《怀素自叙帖书法析解》。读后让我崇敬又崇拜。短暂的邂逅, 漆库德 瞬间的擦肩而过,成为一生效仿的楷模。 韩国有则谚语叫作"饱成的稻穗总是把头垂下的"。自与冯先生接触后,大凡遇到自以为是、趾高气扬、装模作样、无病呻吟、不可一世、大吹大擂、目空一切、牛气冲天之人,统统被我鄙视。

👆关注连云港手机台👆
👆每周更新《家在龙尾河畔》音频👆

END

编辑丨王婷婷
审核丨段潇
来源丨FM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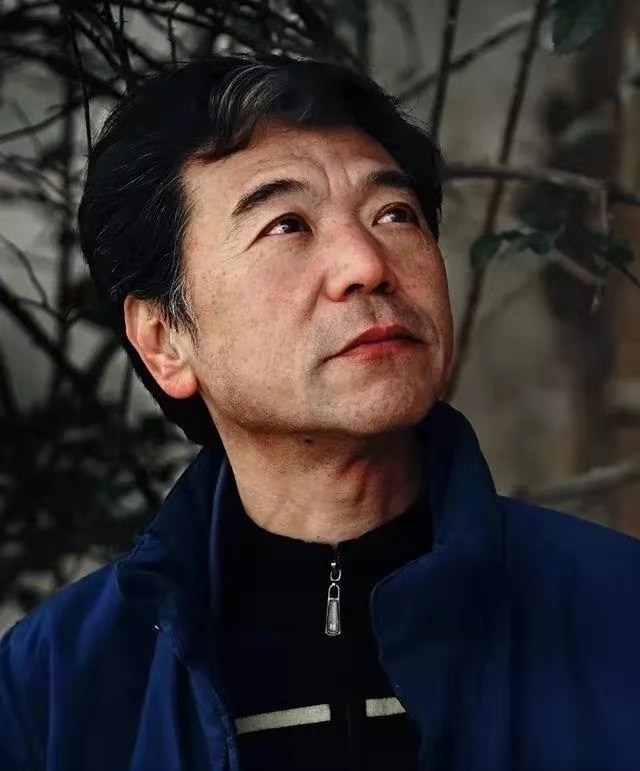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