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山散文集《家在龙尾河畔》第八章第一节|家边邻居殷小狗

「家在龙尾河畔」|第八章 第一节📖

▾ 点击收听 ▾
《家在龙尾河畔》简介
2020年,一部名叫《家在龙尾河畔》的自传体散文集诞生了,书的作者叫张耀山。作品诞生之初是非常之年,诞生之际是非常之时,诞生之作是非常之举。因为这样一本书的问世与这个年景的许多元素有着高度的契合,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家在龙尾河畔》始终以平民生活为底色,热烈地拥抱生活,处处可见血浓于水的家乡情节,绝不像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找不到自己的原乡。正是那些琐碎的、点滴的生活细节,构建了作者极尽渲染的龙尾河畔泛黄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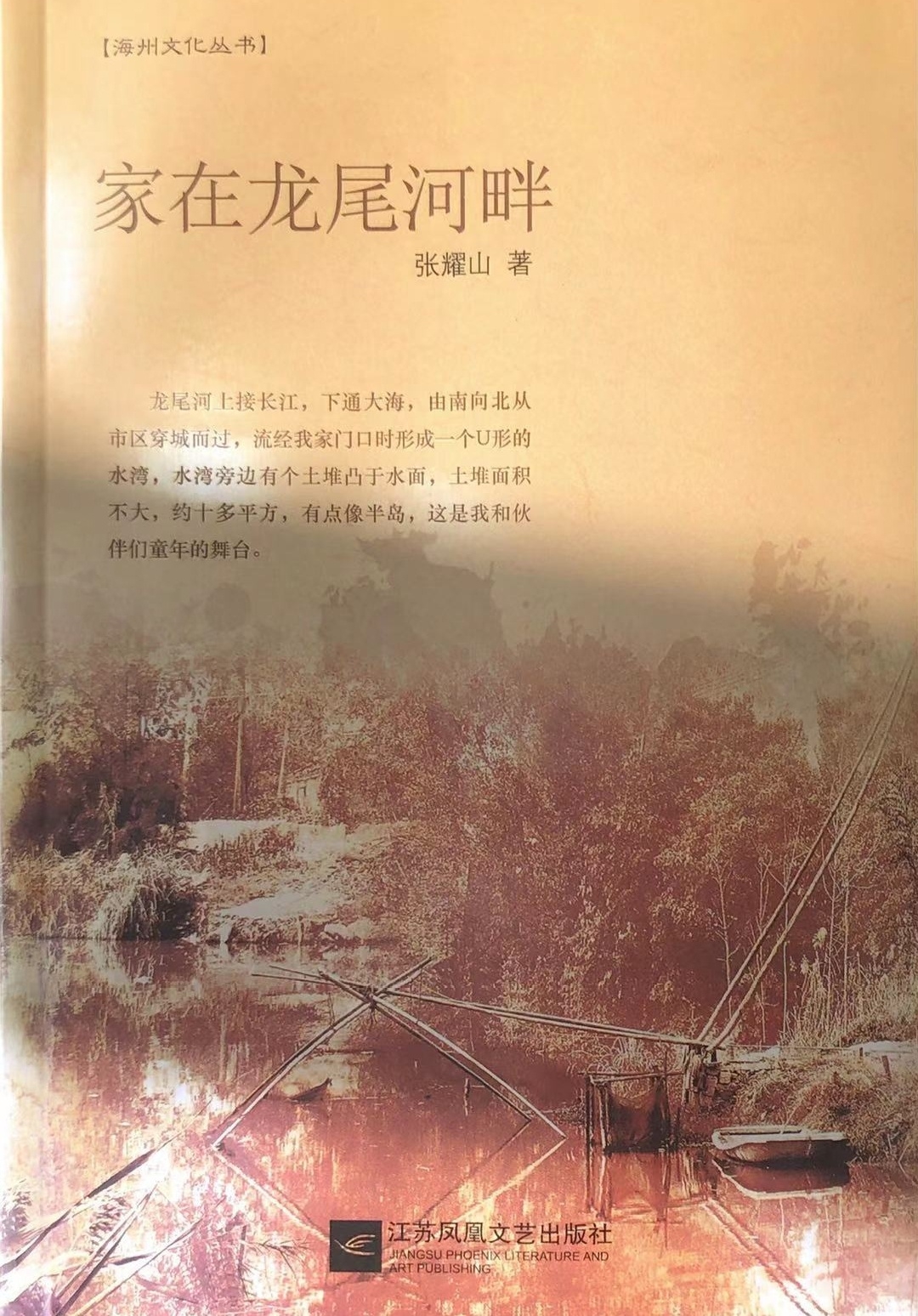
- 关于作者 -
张耀山,1955 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生于连云港,曾就职于连云港市文联。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十三届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连云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连云港市安东书院院长、连云港市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他认为家不是由物质堆砌起的空间,家是情感的载体,是灵魂的栖息地,是精神的乐园。

家边邻居殷小狗
"殷小狗"是他的乳名,在家排行老小,或许是生于狗年,就叫他"小狗"吧,因为这与十二生肖合辙。果真如此的话,那算是有点学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妈生他的时候,正好有一条小狗打他家的门前走过,触发灵感就顺口叫他"小狗"。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晚年得子,就当狗养着吧。这名字本身太有随意性,可以有许多猜测。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已是"老狗"了,邻居们还习惯管他叫"小狗"。你要喊他的名字殷古泉时,他的反应会有短暂时差,先是愣一下然后才知道是叫自己的。
我家与小狗家隔了一条圩子。他家在圩外小斜路上,是贾圩桥通向通灌路的便道。中学时代我经常背着书包从他家门前路过。看到了相互会打个招呼,但少有交往。
我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成为好朋友是从一本字帖开始的,用后来时尚的说法叫作"笔中情"。
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时,我看到竹匾里有一本字帖,是线装本,有些发黄且不完整。封面上写着《千字文》几个大字,落款处是"中村春堂"。我不清楚"中村春堂"是编者还是书写者或者是出版商的斋号。打开一看正草隶篆四体,而且. 是日本货。他爸说是日本鬼子逃跑时留下来的,撕下几张擦屁股,软软的很舒服,"小狗子"拿它当宝贝一直没舍得扔掉。

我虽然拿了许多年毛笔,临写的范本是父亲的手迹、街头的大字报还有伟人的题字,从来没见过字帖,更没临过字帖。由于字帖的吸引,路过他家时总是待上一会儿。
时间久了,我俩的关系也近了,我向他借字帖,他不小气可能也不知道它的珍贵,爽快地答应了。说是借的,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橱里,估计他早把这茬事给忘了。
受我的影响,他曾经爱好过一段时间书法,但他缺少艺术天赋和才情,很刻苦却不见长进。不过他的头脑很灵活,动手能力特强,无论是银匠活还是锡匠活都干得很棒。他喜欢玩无线电等高端的玩意,能根据《无线电》杂志上的图形自己购买元件,组装一只小船,用手中的遥控器指挥小船的走向和速度。下水试验那天,他姐姐门前的水塘边里三层外三层有大人也有小孩在此看热闹。无线电发出的电波被有关部门监测到,居委会主任硬说是和台湾在联系,由于家庭背景复杂,十三四岁的孩子被抓到派出所蹲了一天一夜。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说想买个相机,可是所攒钱不够,提议我俩合资。他开导我说,相机买来不久就能收回成本。怎么收回,我不懂也不想问,倒是买相机的创意深深触动我的兴趣。那时每到解放路上有大型集会,我俩都会结伴看热闹。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高个男子身上背着两台相机,一台是"海鸥"双镜头的,另一台是单镜头,上面写着洋字码不知道是什么牌的。两台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我俩跟在高个子身后,穿梭于游行队伍的洪流之中,直到集会结束了才怏怏而去。我俩羡慕的不仅是那高个男子,还有他手中的两台相机。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拿着两个相机的高个男子是后来连云港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来俊华老师。
我俩倾尽所有,合资买了一台双镜头的珠江牌相机。这个品牌仅次于海鸥牌,因为海鸥牌相机要凭计划供应,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其实,两种相机除了品牌认知度不同外,价格与性能没有多大区别。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意。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他家,他没想到我会来得那么早,桌子上摆满相机的零件并按拆下的顺序写上序号。他看出我的担忧,安慰我让我放心。事已至此埋怨也无济于事,由他折腾吧。
他心灵手巧胆子大,生存能力强。他的母亲因是某非法组织的头目而受到惩罚(经查后,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必须一人面对。
几天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找我。自行车是从学校对门的顾大爷家租来的。由于用户口本作抵押,租金不用预付。买了相机之后我俩几乎身无分文。
他强行把我拽上自行车,出市区,沿着蔷薇河堆一路向西,路上没有对话没有交流。我知道他的鬼点子多,一切由他摆布。约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岗埠农场一个很大的连队,有几十户人家。农闲时节,农民窝在家里,一看城里来了两个小青年,骑着自行车还背着相机,就都走出家门看热闹。只见"小狗子"找到一块空地,在两树之间挂上早已准备好的白色被单,吆喝要为农民拍照片。土生地长的农民没见过这等新鲜事,开始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稍后纷纷排队拍照。一些少妇少女拿出自己压箱底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偌大的空场上一片花花绿绿在涌动。从上午十点来钟开始一直拍到太阳快要落山,光线不符合拍照的条件,没有排上队的部分村民很失落。"小狗子"安慰他们,送照片来时再拍。一句话的承诺给他们一星期的等待。我们回到家中按照《摄影手册》的要求,买来显影粉定影粉,把门窗蒙得严严的,不透一点儿光。反复试验,加班加点。一个星期后,我们如约而至。这次场面更加壮观,附近连队的村民听说有此好事,早早在空场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通过盘点,我们不仅收回了投资的成本,还略有盈余,令人欣喜的是还赚了两竹篮鸡蛋,这是没有现钱却又想拍照的村民拿鸡蛋兑换的。要知道,鸡蛋在当时尤其对城里人来说是奢侈品,不仅买不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买不起。只有在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才能凭票购买一点儿。连续两个星期拿鸡蛋回家,引起父母的警觉,我实情相告,可把父母吓得不轻。这种行为如被告发是要被严厉处罚的。
一场以赚钱为目的艺术实践活动就此打住。
我俩交往的初衷是出于对书法的共同爱好,我坚持下来了,书法成为我的职业,是我唯一的谋生手段,虽没有什么作为倒还体面。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小狗子"了,听说他前些年在捣鼓日本旧空调,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据说收入颇丰。
👆关注连云港手机台👆
👆每周更新《家在龙尾河畔》音频👆

END
编辑丨方婧瑄
审核丨段潇
来源丨FM90.2





最新评论